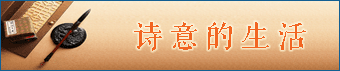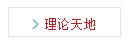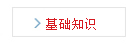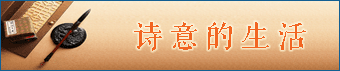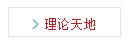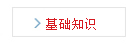对联的语言与命意
刘太品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对联虽然是一种包含了文学性、实用性和谐巧性的特殊文体,但究其本质仍然要归于文学的范畴和诗歌的体裁,依然要遵守文学创作的一般性规律。所以,对联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的形式来表达特定主题的文学样式,而这里所说的“特定主题”,也就是“命意”。总之,如同人类个体存在精神和肉体的“形、神二重性”一样,对联文体也与其它文学作品一样存在语言和命意的二重性。
语言和命意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共生体,就文学范畴内而言,不存在没有语言的命意。反之,也很少存在没有命意的语言。但在对联文体中,有两类极端情况要除外:一是在所谓巧对中往往只有文字技巧的层面,不具备任何的命意成份,也就是说其语言是不表达任何特定主题的纯文字游戏。当然,巧对和无情对之所以用“对”来命名,说明它们与对联文体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诚如梁章钜所言:“是对也,非联也,语虽通而体自判。”二是所谓“合掌”的对联,相同的信息,上联已经表达过了,按现代信息论的观点,下联便不存在任何的信息,也就是说下联只是不包含命意的语言了,所以对联文体才视合掌为大忌。鉴于此,我们在探讨对联的语言与命意这一问题时,要排除掉这些极端的情况,主要从文学类对联和实用性对联来分析其语言和命意的关系。
文学的语言一般总会承载着一定量的命意,但同样长度的“文”中所包含的“意”的多寡,有时却相差悬殊。空洞的词藻和陈俗的套话,语虽多而意寡,而鲜活凝练的警句,却能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我们把抒情、说理和写景类的联语统归为文学类对联,原因在于这类联语承继了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基本功能,并且传世的前人对联作品中,通常以这类对联的文学价值最高。抒情联如刘念台“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说理联如曾国藩“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写景联如郑板桥“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都很能打动人心。至于情景交融、情理并生的那些作品,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如顾复初“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再如陶澍“此即濠间,非我非鱼皆乐境;恰来海上,在山在水有遗音”。
与正统的文学体裁——如诗词——相比,对联在精神层面,也就是命意方面相对要弱小一些,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主要原因在于实用类的楹联大多在语言上陈陈相因,不仅缺乏新意,更重要的是缺乏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实用类楹联作品文学性的减弱,首先表现在其语言的“陈、俗、庸”上,因为使用频度极高的缘故,实用性楹联很难时时处处创出新意,所以陈言、俗语和套话成了实用楹联的一个特征。特别是各类实用性楹联在长期使用和流传中,已经形成了各自的习惯用语和常用意象,这就更加剧了这一倾向,比如贺寿必言“海屋”“南山”,贺婚必言“琴瑟”“凤鸾”,贺新居必言“莺迁”“轮奂”等。当代征联活动中的参赛作品,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实用楹联”,因为能在语言上拓出新境、引领潮流的作者毕竟是少数,所以“克隆”获奖联作中的词语便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从而在“老干体”的俗套之后,新形成一种“征联体”的俗套。征联体的特征是对获奖联作精彩词汇的大量袭用,形成一个时期的“热词”“流行词”:比如一段时间出现好多以“三代表”对“两文明”的对联,一段时间又出现大量“中国梦”对“小康图”或“上河图”的对联。征联体另一个特征是袭用、滥用修辞手法,也就是生硬和勉强地套用别人用过的修辞手法,如有段时间满纸 “××点题”“××作序”“××写跋”“××钤印”一类的拟人手法,足令阅稿者不胜其烦。修辞手法必须要符合读者的形象思维,比如说“政策铺春”可以理解,但“创新作序” 便未免太过牵强。再如“皴”只是画山石树干的一种技法,并不能作绘画方式的代名词,但被不少作者当成“万用动词”滥用,其实使用“皴”“揉”等怪僻字,还不如老老实实用“描”“绘”更见稳妥。另外,在句式结构和篇章中的句式组合的层面上,征联体同样存在这类盲目因袭的做法,这里不再细述。
实用性楹联作品文学性的缺失,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命意方面缺乏新意和真意。通常说来,陈旧的语言总是与陈旧的立意相伴随,缺乏创新和独到的立意,才会堆砌陈俗的词藻来完成应景的任务。如春联的“红梅傲雪庆新春”,行业联的“财源滚滚似春潮”等,并非句子本身有什么毛病,被数代人重复无数遍之后的了无新意,才是其毛病所在。对联是形制极其短小的文体,如果参加征联活动,想要在海量的联语中显露出头角,运用新颖的语言和新奇的立意显得尤为重要,陈俗的语言和平庸的立意肯定无法在短暂的瞬间抓住评审者的眼球。
古人有“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之说,炼意,既要炼出新意,更重要的是炼出“真意”。所谓真意,也就是要在作品命意中融入作者真实的情感,联语追求“新意”固然重要,但追求“真意”才是文学创作的真髓。文学就是人学,唯至真至诚,方能尽性,方能合天,方能化人。在对联作品中呈现作者的真实的情感体验,表达对人生经验的理性思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首先肯定,怀真之作,必有可观之处。但其质量高低,还要受精神的高度及语言的精粹度制约。如果表现的是琐碎的情调和偏狭的思想,其感人的程度必会大受影响;如果笔力不够,作品的艺术力量也会削弱。惟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与崇高的精神境界相结合,才能达到高度的艺术美。如左宗棠挽胡林翼联:“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睽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耳!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今期许此纯臣。”胡林翼曾七荐左宗棠,相知极深。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哀恸异常。这种内心自然流露的情感恳挚动人,又能兼顾私谊与大义,故而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学类对联中,景中含情的联语和理中带情的作品,格调更为上乘。纯粹的说理容易陷入空洞的说教,只有融入了作者的人生经验,才能真正说服人;纯粹的写景容易流于苍白的描摹,只有灌注了作者的感慨,才能真正打动人;纯粹的抒情容易成为虚夸的呻吟,只有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才能真正感染人。这就是文学作品“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在实用性楹联中,“有我之境”的作品在格调上自然要优于“无我之境”的作品。如中医联中,“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一联明显比“杏林三月茂;橘井四时春”为佳,因为前者使作者的心胸品格跃然纸上,是典型的“有我之作”,而后者则单纯颂扬医生,并无作者独特的品格与形象在内,是典型的“无我之作”。但是,有些体裁和题材先天就限制了作者性灵的抒发,如八股文是要“代圣贤立言”,就很难展示作者独特的形象。与之相似,当代征联活动中的大部分联作,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写出“有我之作”的可能性,因为大部分征联主办方只是居高临下地花钱来买作者的褒赞,评审时也不希望有鲜明的作者个性特征的作品获奖,因为这类作品不符合他们的主旨和初衷,参赛者此时只是以“写手”而不是以“作者”的身份来从事写作,所以此类作品从格调上来说自然要居于作者自由创作的联语之下。当然,有很多参赛者不甘于这种“无我之作”的写作,努力从语言和立意上渗透进自我的意识和印记,但这种努力在当代征联活动中通常是不成功的。如征联体中还有一种突出“我”的联套,即上联以“谁怎么怎么”来设问,下联则以“我如何如何”来作答,这种突出作者个人意识的参赛联语,起初以其剑走偏锋的新奇也还有一些获得奖项,但时间一长,很多评奖会上就出现了见“我”字便淘汰的情况,哪怕是作者把“我”解释成主办方或是第三方的普通观众,也很难扭转这种征联活动主办方对参赛者主观意识的排斥。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用性楹联中,也存在着适合展露作者真实情感的体裁,这类作品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挽联就是最好的例证。“挽联”是一个被联界模糊使用的概念,应该包含了祭棚、铭旌等处的“实用丧葬联”和宾朋表示哀挽之意的“个人吊挽联”,前者出现于南宋,后者始于明代中叶的李开先,前者与其它实用类楹联并无二致,但后者却更接近于抒情性的题赠联,只不过赠的对象是逝者罢了。这类挽联往往要表现作者与逝者的个人交往,从而展现出作者最为真切的思想情感,有着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这类“个人吊挽联”占据了历代传世楹联的很大比重,其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也是一般“丧葬实用联”所无法比拟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是贴近作者心灵的作品,越是表达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就越具有更高的艺术品格。
以上分析了文学类联语和实用性联语中语言和命意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我们通过还原一副对联的创作过程,从而提示出语言和命意在创作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
对联文体在本质上是从属于诗歌体裁的,所以对联虽然包含了实用和谐巧的成份,但仍要受“诗言志、词缘情”这一文学传统的影响。文学类联语固然以抒发真情实感为尚,实用类楹联特别是征联虽然局部对“真意”有排斥,但却同样推崇“新意”,也就是说不能缺少了命意的存在。所以总而言之,对联文体的创作,应该是一个语言与命意相互作用的过程。
社会生活是对联的原始素材,作者的思想与情感是对联的灵魂,而语言,则是连接这两者的津梁。我们在创作对联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搜集、筛选素材。如果是景观联,我们要了解景观的外形、名称、所在地、历史沿革、主人情况等素材;如果是挽联,我们要知道逝者的年龄、身份、事功、家庭环境等素材……准备好素材后,我们要做的是筛选出能为自己所用的部分。这样,对联的材料就准备好了,好比造房子的时候选好了砖瓦门窗等建筑材料。好的建筑,都会体现出建筑者的品味,这个建筑既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也是一个精神的世界。语言即是其物质,而其精神通常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思想,一是情感。思想的高度和情感的质量决定着精神世界的完美程度。怎样把材料砌成建筑,去体现思想与情感,这就得依靠建筑者的手艺,在对联中,就得依靠作者的语言积累量以及语言把握能力。
有没有进行素材的搜集与筛选,以及搜集与筛选是否典型,决定一副对联是否“切”。我们说某副对联“切地”、“切姓”、“切事”、“雅切”、“精切”等,就是说的对联与对联所反映的本体的客观情况是否相合。素材出自社会生活,或者来自于亲身的经历交游,或者由要求撰联者提供,或者根据书籍网络间的记载,等等。出自于生平经历的,往往能写得比较真切感人。而临时提供或查找的资料,往往需要一个内化与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得好不好,对作品的质量影响也很大,前人评价的“如生铁铸成,不可移易”便有很大部分指的这个意思(另外还关系到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素材是作者思想与情感生长的土壤,若离此而凭空想象,则所写对联难免是“无本之木”,空泛而没有针对性,有时甚至给人“不知所云”的感觉。
在我们创作一副对联之初,无论是从心底涌动出一股“我要写”的冲动,还是因拿到了一个特定的题目而出现“要我写”的压力,作者所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命意的问题,也就是说“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意在笔先”,正如张炎《词源》所云“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纯粹的“意在笔先”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必须要按部就班地依照“拟定主题思想→做好谋篇布局→安排上联→对出下联→调整平仄对偶并润色文字”的程序进行创作,但在真实的创作过程中,除了少数超长联大致是按照这种程序来操作外,一般中短联语的写作并非刻板地分成这么多步骤,而是几个步骤混杂在一起,甚至很难分清命意和语言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比如我们读一般作者的联作,有时会出现下联或是下联的某个分句自然、畅达、精警,而相对的上联句子却涩滞凑泊的现象,这无疑表明下联的形成要先于上联。我曾多次表达过这种观点:好的联语是从作者心灵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这种命意和语言浑成一体的喷薄而出,方才称得上是“创作”;而“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从设定主题思想到篇章布局,再到逐字逐句搭建起全联,只能是一种工匠的“操作”。创作是“我要写”,操作是“要我写”,创作是艺术,操作是工艺,创作的作品在格调上永远高于操作的作品。
因为人类是依靠语言而进行思维活动的,所以对联的立意也要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宏观的人类语言,而与命意相对的“语言”则是指狭义的对联语言——所以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所说的命意最初是以局部的句子以及短语和词汇的形式闪现在作者脑海中的。马萧萧先生曾在自己联集的序言中说:“在我的艺术创作中,第一闪念是很重要的,很可贵的,因为它最鲜明,最生动,往往是作品的灵魂所在。”这种最初的灵感虽然可能只是些语汇的片段,但却确定了全联所站的角度和高度,大致定型了全联的篇章布局、语言风格,我们把这些片段放在联语合适的位置,足成完整的对联语句,再调配精工的对偶,然后在上下联的互相调整中完成全联。就这个过程而言,我们其实很难分清语言和命意是孰先孰后的,它们一并在浑沌状态中发生,相互调整,不断完善,使各自清晰起来,最终达成形与神融融然、文与质彬彬然之境界,从而完成了一副优雅的对联作品的创作。
我们前面说到,语言的“陈、俗、庸”是造成实用类楹联文学性不强的重要原因,所以要提高联语的文学性,语言角度来说,就应该尽量追求“新、雅、奇”。这是一种横向的分法,当我们进行纵向上的分类,把对应的三组词拈出比较,我们会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组,关于对联语言的“陈”与“新”。与之相类的表达方式,还有一对,就是语言的“熟”和“生”,若结合起来分析便很容易得出正确结论,语言越是“陈”,直观上肯定越“熟”,但语言“新”过了头,自然会有“生”的感觉。所以对联语言的“新”是相对的,是“新”和“旧”之间的平衡,“生”与“熟”之间的匀称,过于“陈”和“生”都会影响到作品的表现力,这个平衡点的把握,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的综合掌控能力。第二组,关于对联语言的“雅”和“俗”。“俗”与“熟”相近但更趋于浅陋,所以一般的对联语言中要刻意避免,“雅”是对联文学性的一种标志,但在程度上还是分为清雅和典雅,再往上说,就会出现以古奥为“雅”甚至以生字僻典为“雅”的倾向,这其实已经走入了极端和误区。因为古奥必然会影响合意的表达,至于生字僻典,明代吕坤《呻吟语》云:“艰语深辞,险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贼也,后学之殃而术之灾也。”这说明习用生字僻典并非“其人学博而识深,意奥而语奇”,只不过无异理而故作异言、无深情而故作深语罢了。第三组,关于对联语言的“庸”与“奇”。同样,我们也只需要在平实和奇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过于平庸不足以打动人,而过于奇幻则又显得故弄玄虚。更有甚者,有些初学联者为了追求奇崛之气,生吞活剥前人成句,乱用自己并不理解的语汇,貌似高深,仔细寻思要么百思不解,要么啼笑皆非,这其实已经走上了创作的歧途。
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对联作品的“命意”,在具体操作上有两个层次:其一是确定一副对联作品的主旨,也即所谓“顶层设计”;其二是对联中具体语言的寓意。就第一层而言,在对联创作出来之前,命意是它生长的全部蓝图;在对联创作出来之后,命意则成为整副对联的“魂”。如同真元充盈于人体并沿经络不断运行一样,命意也充盈于全联之中,这可称之为“气”;命意同样也沿上下联的各分句及在上下联之间往复运行,这可称之为“脉”。一副联“气脉”的好坏是决定它能否成为佳联的关键。好的“气脉”应该是这样的:气虽充盈,但分布并不均匀,疏密和浓淡之间就形成了铺垫转折与警句联眼的区别,也构成了全联的章法布局;脉虽运行,但速度并不均匀,沉郁与流畅之间便形成了回肠荡气之韵致,也让全联更富有张力。这种命意表面上是由各个分句的寓意和各个词语的含义构成的,但实际上又超出了所有分句寓意和所有词语含义的总和。至此,一副对联作品的完整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已经构筑完毕。
对联的语言和命意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任何失衡,都必将导致对联作品明显的缺陷。意多而言简固然是我们的追求,但当命意过多时,却非极简的文字所能承载,有的作者想法很多,情感很丰富,但在构思过程中不善于梳理,只能硬性堆砌于联句之中,造成联语气脉的拥塞、跳跃和语句的断裂、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语的表达效果。至于文长意短之病,则更应为作者所力避,意之不足,一来可能源于作者文思枯滞,比如有些作者拿到个题目无处下笔,只好先嵌字组词,再敷衍成句的方式写完全联,这当然很难去寻什么命意了。二来可能作者试图以华美的辞藻来补偿命意的不足,但过于眩目的辞藻反而冲淡了原来的主旨,给人以看起来很美但缺乏内涵的感觉,正如南宁张炎《词源》评论吴文英词:“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三来可能是作者不善于剪裁原始素材,进行合理的取舍。比如《联语粹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荫斋所为联,语句极工整,而两联意思每不能相称,曾记在本县高等日,同事赵香甫为其祖父母及母发引,荫斋送挽联云:‘翁姑偕老,得冢妇随侍蓉城,果能上界团圆,琴鹤家声应共话;窀穸相安,免孝子疚心蓬颗,幸藉先灵呵护,石麟地脉自呈祥。’上联意思甚完全,下联只说一安葬,未免意尽词穷矣。香甫属余为改易存之,乃僭易一联云:‘百年偕老,得冢妇随侍泉台,仙界要团圆,琴鹤家声谈一室;七载宦游,与文孙常亲几席,祖风勤诵述,鲍桓遗范足千秋。’下联从己与香甫一面生意,方可对得住上联,且挽之亦觉有情也。”从倪星垣先生所举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下联由于材料择取不当,从而导致“意短”,而改换角度重新组织后,上下联之间的命意才变得匀称了。
总之,若内容胜于形式,联语则会流于直白质野;若形式胜于内容,联语则会流于浮华空洞。我们所追寻的佳联的境界,应该是语言和命意的高度统一,应该是有质量的辞藻与有高度的精神的完美结合。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字,方才是活着的。 |